

编者按
科研是职业科学家才能做的吗?不,人人皆可做研究。这是一位上海昆虫爱好者投稿的“刨根问底”物种鉴定笔记。
作为生活在上海、外贸行业全职工作的一位“虫妈”,她加入“上海昆虫家谱”公众科学项目后,在兴趣驱使、自主学习、社群支撑中,完成了从“入门爱好者”到“上海昆虫审核鉴定官”、“公众科学家”的转变。
看看这次让她获得快乐的“物种研究”吧!
在“虫友”@虎甲妈妈的多次“安利”下,2024年6月8日端午小长假期间,我们虫妈俱乐部的“荒地刷虫计划”终于付诸行动。
这块荒地位于闵行区的元江路和曙光路交叉口附近(地图中红圈位置),由于太过偏僻,几经周折我们才成功会合。

图源:百度地图

荒地寻虫
这块荒地的主要植物是由桑科的构树、桑树构成,其间夹杂着菊科、乌蔹莓和零星的梧桐等植物,茂密的植被中有一条狭窄的小道,深处还有一块块被开垦出的菜地,甚至还有一处猪圈。

调查现场照片,右一为作者
宅小萌 摄
“虫妈们”稍寒暄几句后就各自掏出装备“刷虫”了。热情的虎甲妈妈尽地主之谊,立马就上了“大菜”——在她的指点下,在入口处的构树上我们惊喜地发现了黑点粉天牛Olenecamptus clarus。我们被它清丽脱俗的颜值征服,各种角度拍拍拍。

接下来惊喜连连,有差点被当成蚁形甲的超级迷你的江苏勾天牛Exocentrus savioi,还有桑小枝天牛Xenolea asiatica、暗翅筒天牛Oberea fuscipennis、双斑散天牛Sybra bioculata、肖楔天牛Asaperdina sordida、江苏勾天牛Exocentrus savioi、桑缝角天牛Ropica subnotata、桑黄星天牛Psacothea hilaris...总之这是完美的一天,上海的天牛九宫格目标达成。

意外发现
下午四点我们准备打道回府,没想到荒地居然还给我留了个彩蛋。撤到入口处时,“虫友”们还不放弃想再找一找虎甲妈妈之前看到过的微天牛Anaesthetobrium luteipenne,而我在高温、干渴以及蚊虫的折磨下完全没了斗志,百无聊赖地靠着一棵粗大的构树等他们。
突然发现一只小蜂在树干创口处忙忙碌碌,即使相机靠得很近也没逃走。拍了几张放大看,感觉长相非常酷,复眼巨大,胸部闪着金属光泽,翅膀也泛着七彩光芒,并且把腹部伸进了树皮创口中。

下方两张照片可以看出,这是一只雌性个体,有着狭长的产卵器鞘,直觉告诉我这可能会是一个上海昆虫新纪录,于是掏出随身携带的离心管把它抓了进去。


回到家第一时间导出照片发到“虫友群”里询问,没想到连专注于小蜂的“虫友”T-Ref(福建农林大学)也一时鉴定不出,于是他建议我发iNaturalist,并帮我@了两位“物种鉴定大佬”。两位大佬很快在评论区留言了:


Jeong Jae Yoo 老师(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,小蜂分类学者)鉴定为Callimomoides属,但是不确定是否为松褐天牛卵金小蜂Callimomoides monochaphagae 。而chalcidjyr老师(实为Jean-Yves Rasplus博士,法国国家农业、食品与环境研究院生物种群管理中心)则意见相左,因为图中这只的产卵器短得多。通过比对T-Ref发来的相关资料,我们也确实有此疑惑。

图源:参考文献4

身份揭晓
那我们采集的标本,是不是C. monochaphagae这个物种呢?为了进一步确认它的身份,将它寄给了位于福州的T-Ref。
T-Ref收到后,建议戳穿腹部无损提取DNA。现阶段,各类小蜂的DNA条形码数据库还未健全,因此不一定能通过测序比对快速得到鉴定结果,但这对以后进建库、补充基因信息,乃至未来将研究方向扩展到研究小蜂总科的高级阶元(科与科之间)的系统发育关系,具有重要意义的(这类标本往往可遇不可求)。

T-Ref 摄
之后T-Ref制作了三角纸尖标本,并拍照、测量。后来,他搜索到杨忠岐教授(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)发表的论文中,对新物种C. monochaphagae 进行过描述:
"雌性长5.7—7.6mm,其中2.7—3.8mm是产卵器"
并且论文检索表中说,它的产卵器是腹部的1.2~1.6倍,我采集的这只产卵管长2.043mm,腹部1.844mm,大约是1.1倍,比例非常相近。

T-Ref 摄
又经查阅资料后得知, C属现有分布于澳大利亚的C. fuscipennis,分布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C. robertsi,分布于马来西亚的C. ovivorus和分布于中国的C. monochaphagae四种。其中C. monochaphagae于2014年被发表,分布中国安徽,中国南方其他地区可能也有分布。

图源:参考文献4
所以,结合尺寸、比例、分布地区看,虽然比例略在检索表的范围外,但最符合的就是C. monochaphagae了。比较遗憾的是标本触角断了,无法更进一步的确认。也提醒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标本还是要尽量多采集一点。
当然,我们的问题并未随着物种名的揭晓而完全消失。比如那片荒地并没有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的存在,也没有发现它的寄主:松墨天牛Monochamus alternatus,为什么这只小蜂会在构树上出现?是否意味着它的寄主并不仅仅局限在松墨天牛这一种?
不管怎么说,至此在T-Ref的全力帮助下,这只“帅酷”的小蜂的身份揭开了,它就是松褐天牛卵金小蜂Callimomoides monochaphagae Yang,2014,为我们2024年上海昆虫名录再添一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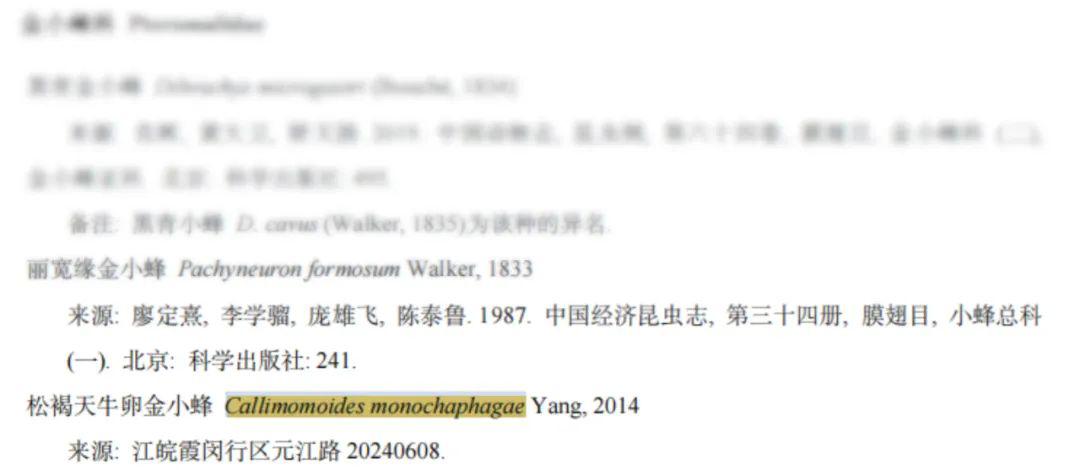
《上海昆虫名录2024版》P.116
之后T-Ref还分享给我了一篇研究天牛卵寄生蜂的文章,文章研究了它们的行为学以及行为学机制,例如寄生蜂在近距离搜索寄主时,一般依靠寄主自身的气味,比如寄主的唾液、粪便、身上的鳞片、产卵器分泌物等所携带的化学信息物质。这些化学信息物质,能明显提高寄生蜂的搜索效率、缩短搜索时间。天牛的卵寄生蜂为了避免发生重复寄生,还会在产卵涂抹标信息素,标记已经产过卵的刻槽。
或许这就是昆虫越来越让我着迷的原因吧,它们小而精致,带给人美的震撼;大量未知新种等着人类的探索,让你能永葆探索的热情;它们神奇的行为,令人赞叹的同时,也能在仿生领域让人类有所借鉴。

上海昆虫
阿直 摄
本次的发现,增加了该种的分布记录,也让这类不引人注意、难以鉴定的小蜂们有更多机会被研究记录。在此,对T-Ref提供的无私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,也感谢虫妈俱乐部好友们,对昆虫的爱好让我们聚在一起共同进步。
上海自然博物馆、大城小虫工作室、上师大昆虫实验室所发起的“上海昆虫家谱”公众科学项目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广的模式,它发动广大市民采集、记录、上传城市昆虫分布信息,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宝贵的科学研究数据。通过参与这个项目,不仅让我们这些业余昆虫爱好者的科学素养得到了提升,同时也帮助科研工作者增加了采集的广度和深度,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。
参考文献:
[1] A New Egg Parasitoid Species (Hymenoptera: Pteromalidae) of Monochamus alternatus (Coleoptera: Cerambycidae), With Notes on Its Biology March 2014 Annals of the 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07(2) DOI:10.1603/AN13150
[2] 张彦龙,唐艳龙,王小艺,曹亮明,杨忠岐. 天牛卵寄生蜂研究进展及应用前景
[3] 公众号:会呼吸的鞘翅 小昆虫大作用:一只寄生蜂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
[4] Zhong-Qi Yang, Liang-Ming Cao, Yan-Long Zhang, Xiao-Yi Wang, Mao-Kui Zhan A New Egg Parasitoid Species (Hymenoptera: Pteromalidae) of Monochamus alternatus (Coleoptera: Cerambycidae), with Notes on its Biology Annals of the 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, Volume 107, Issue 2, 1 March 2014, Pages 407–412, https://doi.org/10.1603/AN13150
/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/

作者:阿直/Tina
“上海昆虫家谱”公众科学项目
物种审核鉴定志愿者
科学审核:余一鸣 上海自然博物馆 展教中心
周德尧 大城小虫工作室
编辑:叁陆柒














